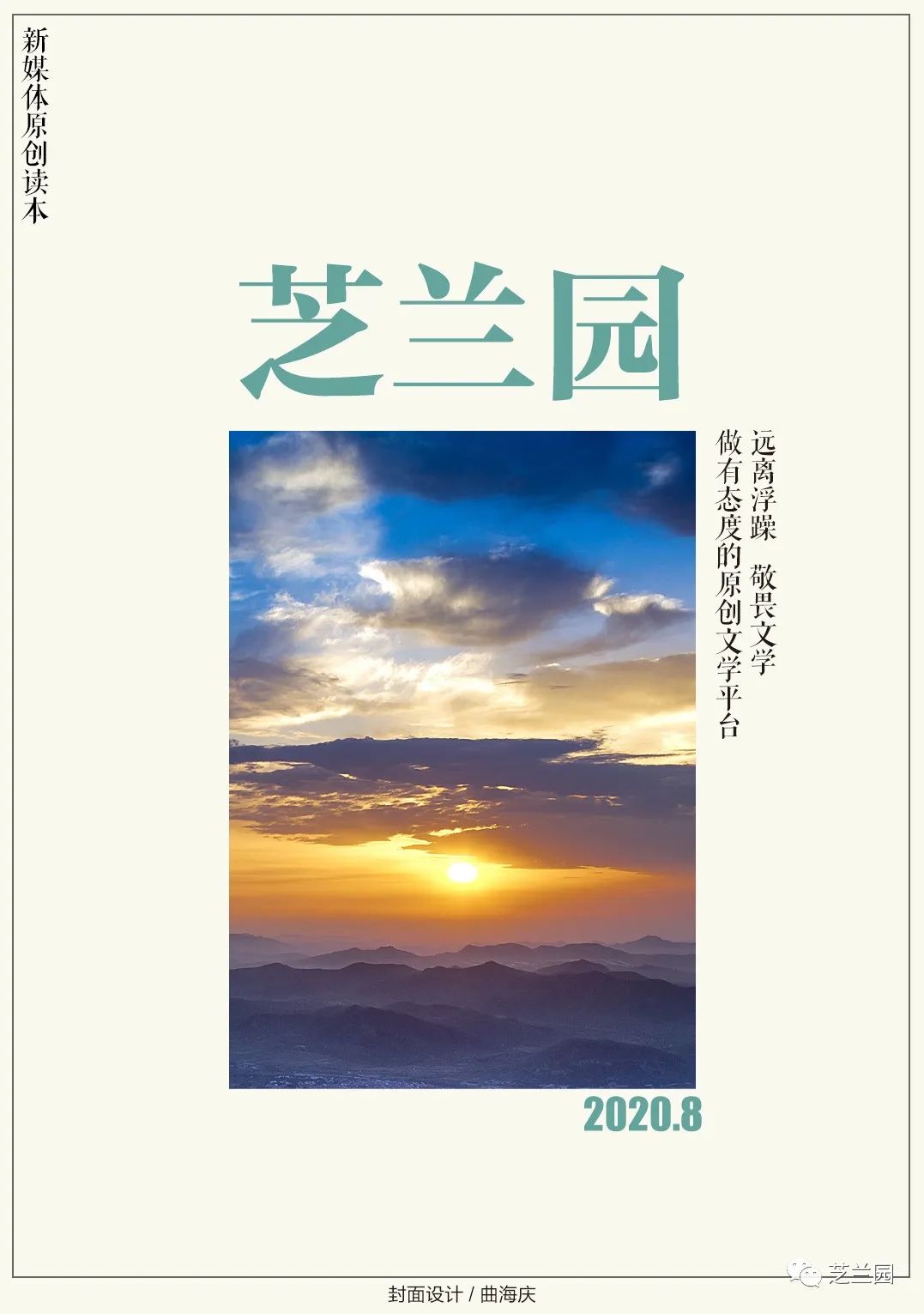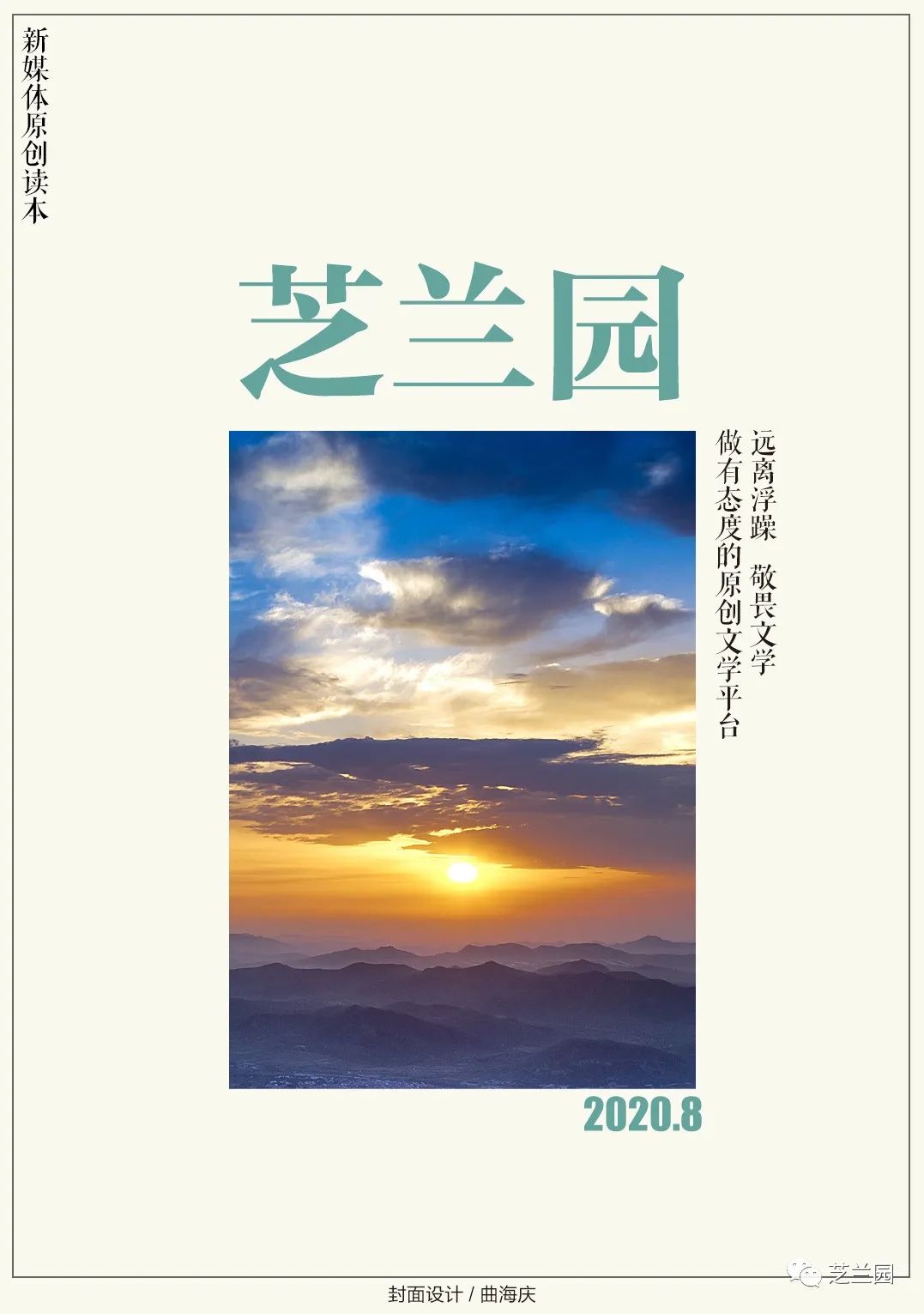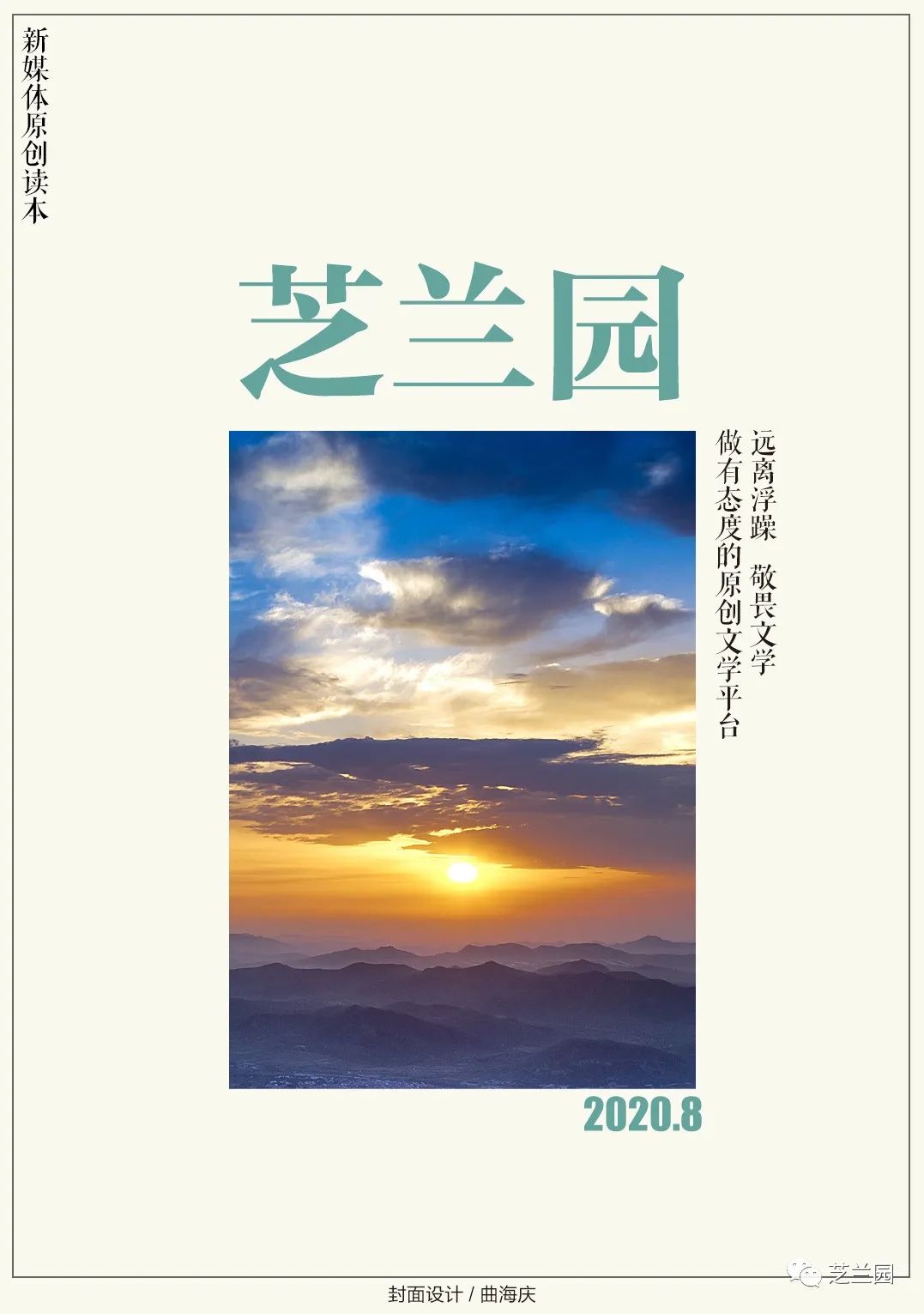
□ 新生/ 文
那时我刚分配到新的单位,这单位是由两个单位叠放在一起办公的大院儿,据说是骑着老城墙建造的,东院墙外探头就可瞧见诺大的一个深坑,坑中地里有时有季节性的庄稼,有时没有,那与有没有大雨颇有关系,因为雨水主宰着它的有与没有,也据说是“造物主”为建城墙用土的杰作。西院墙外的一些地方,也会依稀可见护城河的遗迹。
先生的办公室也是家——这是那个年代公家人常有的待遇,就分配在与深坑毗邻的东排房的一间,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可能稍大一点儿,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个儿,分头,但常有点散乱,脸庞消瘦,脸色白中泛黄,算是病态吧。走起路来摔着两只脚,好像不叫脚着地似的,一下子就要走到目的地。他不能开口,一开口就闸不住门,总要把想要掏出来的东西一股脑儿给你。不过,也不是信口开河,常会ABCD的说出他的道道来,伙计们不知不觉就让他站了C位,这就是气场吧。
不过,他给我吸睛的气场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是个性内向、不善言谈的蜗居男人,就八卦五行来说,如果我与他PK应该是相克或相冲的吧,尽管我不懂卜算之术,仍觉得我俩不是一个“阶级”的贫下中农。我听同志们叫他baosheng,而看他的言行,岂不就是“豹生”!想想吧,咱农村人起名字,就好虎生、羊生、鹿生、象生的,真真儿来说,起名字的家长恐怕连虎连象都没有见过呢。然而,这“豹生”工作起来的样子还真像虎豹似的,威猛的很,怎见得?

每当我走到他办公室门口,就听见嗒嗒嗒的“拍电报”敲击声,哧—呼嗒、哧—呼嗒的异样声,及至走入他办公室,他虽然满脸堆着笑,可看出来那笑是带着惶恐的因子,给你说话时也不再侃侃而谈了,直白说,就是促促的结巴,一边客气的应酬着你,一边眼球不时扫描着那一大叠带字的稿子,就是双脚也不时地颠来颠去,恍然大悟的我,自然尴尬地退出这个“炮火纷飞的豹的领地”,还他个打字、油印、写稿的个人空间吧。
单位的公厕在东南角,我的住室在北边排房第三排,晚上入厕时,自然要经过这“豹生”的住室,但是,我从晚9点看到他屋里的灯光,再到早5点起床路过,那灯光依然是灯光,屋里的那个身影依然呈现的是佝偻。公用水管就在他家门口,清晨我们就去那个地儿洗刷,等他出来,往往见到的是一双红红的眼睛,血丝清晰可见,不,确切地说,狰狞可怕,就是豹子刚下山时的豹眼呀!我看着他说:
他挠挠头,见我一本正经地问,茫然地左顾右盼,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我从来都是正人君子的样子。
“你看你瞪得那一对儿豹眼,血红血红的,要吃人呀?”
他瞬间迷瞪过来,讪笑着说:“嘿嘿,赶写点儿东西,不熬夜赶不过来,有时效的。”说着,耸了耸肩,“你是科班出身,回头给咱指点指点。”那一脸的诚恳容不得你的推辞。
我头脚回家,他二脚就踢沓过来了,拿着他写的东西,一看,是篇通讯稿子,署名是:于报生。
“嗨,我以为你是虎豹的‘豹’,敢情是报纸的‘报’?”
“是啊,我往报纸投稿,叫‘报生’不合适吗?——要不,我改过来?”
我赶忙接口道:“别介,千万别介,‘报生’就好,‘报生’就好啊!”

先生的新闻通讯稿常投向报纸和县广播站,看他以前的稿子写的也就是真实,顺畅,因为他的钻研和努力,后来的稿子艺术性就强了,每当我在喇叭下听着他的通讯稿,我还自嗨的嘟囔道;“不新闻了,我早知道了!”也许这就叫先睹为快呢!
说起写新闻报道,就是个为公众服务的活儿,可他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就乐意干这活儿,以前发表文章不署名,他干的嘛有劲,后来署名了还是一样嘛有劲。我给他的评价是:
这人有虎豹的猛劲,促促地赶着趟儿,从不拖泥带水,不像我有点腻歪——这种精神就是新闻人应该有的素质,否则就不叫新闻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这一生谁也弄不清自己要怎么走路,人生怎么规划也不尽靠谱,算命的更是胡扯蛋。随着时间的变迁,我俩都不在原来的单位了,跳到这里跳到那里的,当然也是组织叫你跳的。不过,他跳的比我欢,职位也比我升迁的快,可我却没有嫉妒他的心,那是人家于兄有虎豹劲儿和新闻的只争朝夕迅捷劲儿,但凡干什么工作,这两种劲儿飙起来就没有不有声有色。咱回过头来,再说他吸引我的气场,难道不就是这个么?
也不是说他的运气点儿就会一直走长生、帝旺①那个段儿,前几年他和我一样有霉运,都得了所谓的“绝症”,他动了大手术,瘦得皮包骨头,突然看到,还有点儿怕人、瘆人,之后才是痛惜:
那么阳刚坚毅的汉子,怎么这么羸弱不堪?说一句话上气不接下气的?
“不过,现时已退休,先生也不用豹劲干什么了吧,身体慢慢会恢复的,就像死里逃生的我,还能爬比四方脑还高的山西画山吔!”我见到他,搂着他柴柴的肩膀安慰道。
他的眼神倏然放出光亮来,萎靡的神情焕发出饥渴的豹子下山的状态:
“老弟,看你红光满面的样子,哪像白血病人!是,是医院误诊了吧?”
“一个医院误诊,四个也会误诊?北京协和医院,那可是国家顶级的医院。”我淡淡地解释道。
都说同病相怜,也许是吧,也不全是。从那以后,虽然好长时间没见过面,可还是关注着他。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消息是沉寂的,我心里边也在忐忑,不知他恢复的到底怎样。
也不知是哪一天,我浏览芝兰园公众号的时候,瞥见《十斤粮票》的文章,看着署名,是先生的。读着读着,眼眶便溢出泪来,心里边一酸,就想起来他笔下我的老领导王主任的事来。他说王主任资助他十斤粮票,那王主任给我的帮助又何止一件?他写王主任,应该的,我知道他是性情中人。

后来,我在看红旗渠报的时候,又看到他写的《散步遐思》,从头看到尾,我的嘴张着竟合不拢,那给我是一个震撼:
他爱好写作我知道,他爱好文学我也知道,因为我们早年就在市作协里。他是副主席,我是秘书长嘛!不知道的是,他的文学底蕴已这么高了,连我这科班出身的都望其项背,看来,这一定又与他的豹劲和新闻的迅捷劲儿不无关系。
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可能疯啦!那作品竟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突突突的向天空弥漫,再加上狂风助力,两年间,热风吹雨洒江天,芝兰园,红旗渠报,时代报告,文艺界,安阳日报,学习强国,甚至大河报网,河南日报,人民日报,都展现了他的心血的结晶,而且每篇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文章体裁也不断翻新,一篇一篇小说都“出笼”了,这还是那个羸弱的病号?
这也让我坦然了,佩服了,因为他的身心在走向康复,他那不屈的生命中向上的基因,在谱写着“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壮歌,他的豹劲和只争朝夕的迅捷劲从那个官场华丽转身,回归了他“报”的生涯,我本“报”来还“报”去,自留墨香在文坛,就像他那一篇大气豪迈的《大爱中国墙》,找准自己新生命的位置,把大爱献给祖国,献给人民。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于先生向上的生命是无限的,就像八百里太行那座房屋旮旯里那颗柿树、黄华神苑那颗800年银杏,虽历经风霜雨雪,仍“木欣欣以向荣”,“裳裳者华,其叶湑兮”②,焕发出她别样的风姿。
②裳裳者华,其叶湑(xǔ)兮:出自《诗经?小雅》。意为堂堂的花,那叶子多茂密呀!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芝兰园):【在人间】新生丨“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