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培,现年96岁(1928–),李一氓次子。航天科工集团三院原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父亲李一氓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同乡好友李硕勋和何成湘。
父亲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着党的文化工作和特科工作。母亲毛一民(原名毛温如,1903-1966)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大革命时期在湖北汉口省妇协工作,并与父亲相识。1926年二人结婚后前往上海。1927年10月后,母亲也成为上海特科的成员,掩护、配合、支持父亲的工作。
我父母养育了四个儿女:哥哥李世滨和我,还有两个妹妹。
1930年5月,我党为贯彻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决定,要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为了保障安全,中央特科精心设计了一套会议安全保障方案,由父亲李一氓考察和出面,租下了会议举办的房子,并由父亲去做这个用于开会的房子的主人。为此,我们一家就临时搬进了这个开会的房子里。当时,除了父亲、母亲、哥哥(李世滨)和我以外,家里还多了一个叔叔和一个姑姑,他们就是由组织安排充当我父亲的弟弟的赵毅敏和我父亲的妹妹的李一超(又名李坤泰),这样六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庭以便掩护这个会议的召开。会议进行了10天,参加会议的代表共约50人。后来我才知道曾经的临时姑姑李一超就是后来东北抗联的巾帼英烈赵一曼,叔叔赵毅敏则是我党宣传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我于1928年11月生于上海,可以说是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仅存的见证人了。
1932年9月,父亲接到组织上的指示,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后来随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自从父亲离开上海后,母亲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外,就是默默祈祷我父亲平安无事,希望日后能有团聚的一天。
后来,上海的党中央遭到多次破坏,失去了组织联络,生活来源也断绝了,一个妹妹夭折了。1934年3月母亲不得已带着年幼的我们兄弟和妹妹踏上了回父亲老家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的征程,途中,另一个妹妹也因病无钱救治夭折了。
回到彭县后,母亲在中学当老师以维持生计。抗日战争爆发后,母亲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彭县成立了妇女会,号召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党组织誉为“彭县巾帼双娇”之一(另一位是李启华同志)。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同志让父亲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做川军刘湘的统战工作。1937年8月父亲以公开的身份回到了成都,完成毛泽东同志交代的任务,除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父亲还携带了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给川军中其他旧相识的信件。
在成都时,父亲从他的好友王季甫处知道我们母子已经回到彭县的消息。于是,他在1937年8月的一天匆匆赶回了彭县看望我们。
在音信全无、分别5年后,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时的我已经对父亲感到生疏了,加上父亲的形象又有了一些变化,不是母亲告诉我叫“爹”,我还真不可能认得出来。见面后,我们一家都喜极而泣、感慨万千,心情的激动难于言表,可惜这时两个妹妹都已夭折了。在和父亲相处的短暂时间里,9岁的我从此知道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和他从事的事业。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由于父亲曾以共产党的公开身份到成都、彭县活动,我们家在彭县继续住下去会有很大危险,所以党组织决定让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及我的堂兄李槐之(1919-2007年,原名李世传,是我二伯父的长子),一共四人奔赴延安。
1941年初途经某地时,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报纸上刊登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因为父亲当时就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所以全家非常焦急。
1941年3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鉴于当时周围环境的险恶,办事处的同志嘱咐我们不能迈出办事处大门一步,而且每个人都要改名换姓以掩饰各自的真实身份,所以我们无法问关于父亲的消息。4月,我们终于抵达延安。
到延安后,母亲立即带着我们去找在上海时就认识的陈云、李富春等同志了解父亲的情况,得知父亲已脱险,仍在新四军工作时,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组织上根据我们的情况,安排母亲去中央党校学习,李槐之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哥哥李世滨和我则去延安自然科学院附中学习。母亲不久去鲁艺幼儿园担任主任。1944年7月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同志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被派往东北地区工作,同时,组织上根据我们兄弟的情况,分配我哥哥李世滨担任中央机要局译电员,我到中央军委三局工作。
当时中央军委三局总台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军台,是代表延安党中央与各解放区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另一部分叫党台,是代表党中央与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也称蒋管区)的地下党的电台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我被分配到党台工作。从1945年9月一直工作到1949年7月工作了近4年时间。
党台工作的特点是工作时间都在深更半夜,对方的信号比较弱,因为他们受到限制,不可能有大功率的电台。对方的工作频率不是很固定,最重要的是必须速战速决,尽量减少对方的工作时间,以保护对方的安全。这就要求在党台工作的同志耳聪目明、头脑反应要快。工作时必须集中精力,心无杂念。这种精神状态对我以后的工作与学习起着很重要的影响。
自从调到中央军委三局所属的总台,让我对父母当年从事的地下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面世。我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更加充分了解了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如何的在险恶环境下与延安总部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的。自己就曾在延安这一端,接受着这些不曾谋面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宝贵情报。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的原型名叫李白,他的电波就是由我们小组负责接收的。每每想到这些,心中充满了对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们的敬意,对那些牺牲在黎明前的李白们,更是敬佩与惋惜。
 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军委三局总台负责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工作者合影(后排右四李世培)
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军委三局总台负责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工作者合影(后排右四李世培)
1946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我哥哥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战场,我则于1947年跟随中央军委三局过黄河撤退至晋绥解放区,1948年4月又随罗青长、童小鹏同志抵达晋察冀解放区的西柏坡。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直到在河北平山县时,接到过父亲从东北托人给我们带来的两本书:苏联宪法及小说《旅顺口》,还有他让我们好好学习的传话。
这时,我已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并于1949年4月随中共中央社会部到达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长李克农同志告诉我,他与我父亲在上海时曾在特科一起战斗过,话虽不多,但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当时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节节败退。昔日的国民党统治区已回到人民的手中,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回到了党的怀抱。因此,工作量在减少,所以存在着改变工作性质的可能性。这时,我虽然已经超过20岁,但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到学校求学读书,以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适应今后变换的工作。
1949年6月,父亲奉调至北京,哥哥李世滨和我这时都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织上通知我们去见父亲。从1937年8月到这次见面,又过去了12年,对人的一生来说,这12年是关键的成长期。虽然父亲为革命转战南北,无法伴陪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在党的抚养与教育下健康地成长,不仅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而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父亲为此感到欣慰。见面后,我向父亲提出希望继续读书提高的要求,得到了他的赞许。一个月以后,组织上通知我调离中共中央社会部去学校读书。
这样,我就开始了八年的求学读书生活,其中三年在国内的大连大学工学院,五年在苏联的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学习期间,我还了解到曾任中央特科四科(交通通讯科)科长的李强也曾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学习。我党历史上第一部电台就是李强研制的,他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奠基者。李强在莫斯科学习成绩优异,发明了《发信形线》,又名“李强公式”,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了轰动,被苏联政府升为研究员,是当时苏联七名无线电专家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与骄傲。前辈的事迹激励着我勤奋学习。1957年7月回国以后就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1956年哥哥李世滨(右)与李世培在苏联莫斯科合影(当时李世滨在外交部工作,李世培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学习)
1990年8月父亲因病住院,我知道后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原以为只是一场小病,没想到这次竟成为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父亲于12月4日晨在北京医院去世。闻讯后我当即从天津赶往北京。到家后,我看到了父亲的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这是乔石同志和夫人郁文同志去医院看望他时,由他口述,郁文同志记录后父亲签字确认的。
看到父亲的遗嘱后,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父亲生前不以位高而自傲,不以才高而自诩,礼贤下士,平等待人,不计进退淡泊名利。对后事的安排将他的优良品质一以贯之,低调处理,不事张扬,实事求是的只要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称谓,同时又不保留骨灰,而是将其撒在曾经战斗过的淮阴大地上。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用他六十五年的革命人生诠释了“老共产党人”这一称谓丰富的内涵。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寒江子独坐):十七年间我和父亲李一氓的两次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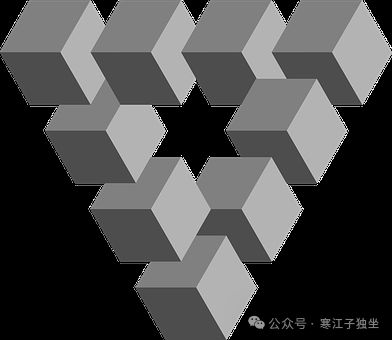

 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军委三局总台负责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工作者合影(后排右四李世培)
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军委三局总台负责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工作者合影(后排右四李世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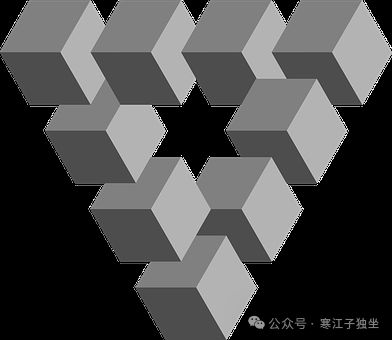

 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军委三局总台负责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工作者合影(后排右四李世培)
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军委三局总台负责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工作者合影(后排右四李世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