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宝追踪:寻觅细节里的历史回响
文 | 王雪霞 刘晓立

国宝:《赵城金藏》
北宋官版蜀刻《开宝藏》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刻版大藏经,是中外各版大藏经雕版的鼻祖和依据。而《赵城金藏》则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忠实保留了《开宝藏》的原貌。雕版于大定十三年(1173)工毕,供养在山西赵城(今属洪洞)县广胜寺内。因刻于金代,发现并收藏于赵城广胜寺,故名《赵城金藏》。
《金藏》初刻成时6980卷,《赵城金藏》现存不到4900卷(国图原著录4813卷),是世界上流传至今保存年代最早、现存卷帙最多、最完整的一部,为海内外孤本。而《开宝藏》久已不传,散佚殆尽,残存于世仅十二号十三件,今借现存《赵城金藏》得以重睹千年前《开宝藏》之风采,实在是功德无量之万幸。
1935年,释范成和徐森玉(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等人借出《赵城金藏》三百余卷展出,并择其罕见经典本影印《宋藏遗珍》出版,引起了轰动效果,从中也可窥见《赵城金藏》的价值。该影印本由朱庆澜、叶恭绰题写书名,因“所刻精籍多有碛砂藏所无,亦有各藏所无者”,故“择名曰《宋藏遗珍》,不忘所自也”。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同礼、叶恭绰等人在合撰缘起中称:“其摄收之弘博,甄选之精严,虽当残缺之余,犹令人惊叹不已。有梵经佚典,有法相秘文,有古德未见之专书,有历代失编之要录。兹辑出四十六种,都二百五十五卷,亟用新法影印,分为上中下三辑,约一百四十册。海内耆硕力赞其成,巨著巍然重兴于世。”

细节:历史的真容
当年 的“抢经”过程有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佐证。纸上数行字,故事的背后却并不简单。在李万里三十余年的追寻中,他有了新发现。
当时抢救经书为何能够成功?在李万里看来,首先在于从提供情报者、决策者到执行者的文化自觉与完美配合。
当年提供抢经情报的人是穆彬,原名马殿俊(曾任太岳区二地委敌工部长),他当时受史健派遣,潜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李万里曾走访赵力之(接替穆彬任铁北办事处主任),并听他回忆称:1938年史健任介休县委书记,大刀阔斧,很有魄力,时间虽短但建立了四个区委,对在介休打开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知人善任,努力培养穆彬,凡来自穆彬的情报都引起史健的格外重视,可以说,二人生死之交的信任是抢经成功的前提。
面对情报,若没有一定文化素养及认知高度,也必然失之交臂。曾任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张天珩说:残酷“反扫荡”的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每天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长远眼光尤为难得。李万里介绍说,这批经卷虽然珍贵,但是“当年非专业的驻军,每天的任务就是打仗,擦肩而过也不会被苛责”。史健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是有其特殊渊源的。史健本人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父是开明士绅,曾创办所在县首所女子小学和图书馆,还曾任当地劝学所所长、商会会长多年,雅好收藏。
曾任太岳区一地委秘书长的李纯也回忆说:感到史健在政治上很敏锐,特别是在对待“大藏经”的问题上,非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不可能做得这样出色。
因事关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尤其是此事发生在平复“十二月事变”余波的时候,容易引发新事端。史健考虑周全,得到消息立即向区党委书记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上报延安得到中央批准后,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将任务交给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地委机关干部入寺取经,洪、赵两个县大队掩护,赵城二区组织的干群驴驮运输队接应,五单位密切配合协同虎口夺经。四千多卷《赵城金藏》全部人背驴驮,经石门峪运抵安泽亢驿的二地委机关。可以说,抢经的成功既离不开提供情报者穆彬与指挥转运者史健的珠联璧合,更离不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果断决策。
其次,抢救经书的成功还在于八路军在艰苦的反扫荡中坚守“人在经卷在”的铁律。
有一个细节是李万里在寻访后觉得需要格外重视的。他发现人们普遍关注抢经当晚的传奇,却往往忽视反扫荡中的风险。在反扫荡的两个半月时间里,三天不见一粒米,只有各种野菜野果充饥是常有的事儿,可据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回忆,为保护“经书”,在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对大家讲:“保护好经卷是一件大事,每个人都要背几卷经。”还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每个人背负20余卷重达40斤的经书,机动灵活性大为降低,在命运多舛的辗转中风餐露宿,在亢驿、马岭、泽泉、合川、白素、热留一带山区与敌周旋,战士生命与《赵城金藏》都有命悬一线的风险。反扫荡中,史健始终与大家同甘共苦,危急时刻过白素村旁涧河,既无桥又没船,成为阻拦行军的大障碍。而当时的涧河河宽100多米。先遣队员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大家扶持鱼贯而行,经卷都顶在头上牢牢扶住,生怕弄湿而小心翼翼。史健执意断后,非要等大家都过完才走。
此后经卷辗转多地,直至194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才最终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
再次,得到扫荡时坚壁清野的藏经洞——娘娘庙的庇佑。
尽管地委机关几十号人两三匹马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在反扫荡时背经转移,但仍带不走全部经卷,剩下的只得坚壁清野,至于藏匿处细节一直未被披露,而这也成为悬于李万里心中的一大谜团。
2014年2月,李万里随亢驿村支书黄才恒,来到亢驿村西小马岭“二区区公所”窑洞前。他了解到,扫荡归来的《赵城金藏》曾存放于此一夜,未回地委机关。中途卸于此表明坚壁清野的经卷就在附近,这大大缩小了范围。
2017年7月16日,正值酷暑,在亢驿村黄才恒和羊倌郭秀林带路下,李万里随国图“寻根小组”爬上亢驿南山小马岭的娘娘庙,终于目睹了三孔石窑的风采,原来反扫荡中实在带不走的经卷就隐藏于此,彻底解答了埋藏心中三十年之疑窦,这也成为“重走金藏路”中的重大收获。
据黄居斌(1923—1981,时任区机要交通员)生前对儿子黄才恒等所讲,他从县委的地下交通站受领一封加急鸡毛信。领导嘱托此信非常重要,比性命还珍贵,绝对不能有闪失,让他躲过日本兵的搜查后,交到马岭的区公所,并要求他通知东湾村樊瑞、亢驿村范志伟、南湾村张福保来开会,传达信中的内容,就是布置当夜向二区区公所转移经卷,组织30多位民兵在麻家山黑虎庙,接应反扫荡归来的经卷并存于区公所内,于第二夜与娘娘庙藏经汇合,沿神父岭、关道沟、中峪店移送到位于沁源的太岳行署。黄居斌还到神父岭联系沁源的接应人马,运经途中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白天走,小心紧张而又神秘。前面部队开道,骡马挑担居中,民兵殿后护卫。
2010年出版的《安泽文史资料》第八辑中记载:“《赵城金藏》运至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后,暂时存放于亢驿南山的有三孔石窑组成的娘娘庙内。”“在亢驿存放的两个多月内,亢驿村武委会主任张善玉积极配合民兵黄居斌、郭大来、阎安政、宋宗宪等都参与了放哨执勤……他们在马岭两侧山头上站岗两个多月。”
细节一点点再次浮现,历史的轮廓更加清晰,而李万里也愈发认识到这段历史的意义。“或许,文博单位认为保护文物是岗位职责所在,可是仁人志士,出于对学术和对国家文化的认同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在浴血奋战生死未卜的日子中,主动抢救出这么珍贵的典籍,更是可歌可泣、令人赞叹。”李万里感慨, 这次成功抢救一洗圆明园明火执仗被抢掠和敦煌文物被巧取的前耻,成为中国文化和文物保护史上的典范,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一场与军事大捷相媲美的文化战线上的胜利,是中华儿女共同引以为豪的成就。

保护研究:最好的回响
如今,《赵城金藏》存藏于国家图书馆已70多年,是馆内的四大专藏之一。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研究专家李际宁在受访中谈道,对《赵城金藏》仍旧有许多问题值得挖掘。“首先,对于《赵城金藏》史的研究需要深入。当年蒋唯心做了一些研究,而我们现在研究条件更优越了,也有了一些新史料,可以用新的史料结合《赵城金藏》的原件,再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一些深入挖掘,比如广胜寺僧人到大都去请印回来的“赵城藏”,与现在存世的《赵城金藏》是否完全是一回事等。另外,对《赵城金藏》文献内容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从《赵城金藏》本身来说,有什么特点、价值;另一方面,《赵城金藏》与《开宝藏》有什么关系。”李际宁介绍说,《开宝藏》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次就刻完的,后来经过了一些修修补补,又经过后世多次校勘,导致早期《开宝藏》中的文字已经发生了改变,而这些改变延续到《赵城金藏》和《高丽藏》中。“我们今天借助《赵城金藏》和《高丽藏》可以反过来研究《开宝藏》的历史,也能够研究《开宝藏》对《赵城金藏》和《高丽藏》的影响。从文献方面看,值得做文献学方面的比较研究;从学术史方面讲,值得做从写本大藏过渡到刻本大藏的脉络研究。”
李际宁提出,从保护修复方面看,1949年到1965年,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抢救修复《赵城金藏》,但从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赵城金藏》来看,还有一些残片仍需整理修复,有零星的残渣可以考虑放到一个容器中进行保护保存。
从某种意义上说,事情发生以后便凝固成历史,唯古籍借助印刷得以传承。李万里也特别提到,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中华大藏经》出版发行,使《赵城金藏》得以流通,被广泛研究、推广,这恰恰说明历史并没凝固,它还活着,并不断向外传播。《赵城金藏》的故事带我们走进那段已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理应很好地研究它、传播它、传承它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响。(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李万里先生寻访记录,特此鸣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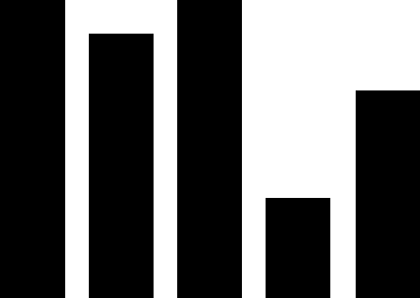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藏书报):国宝追踪:寻觅细节里的历史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