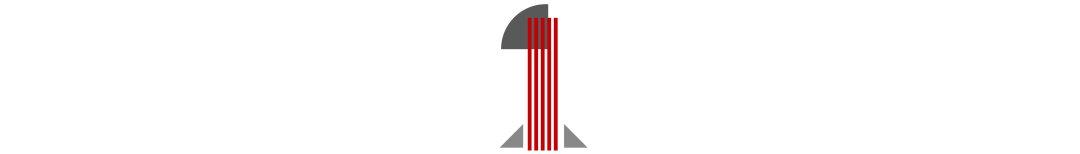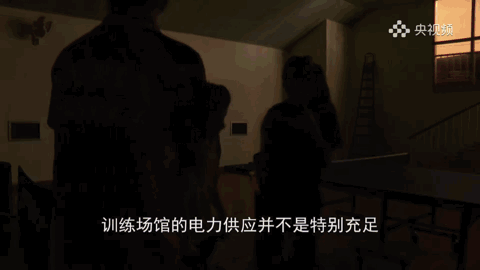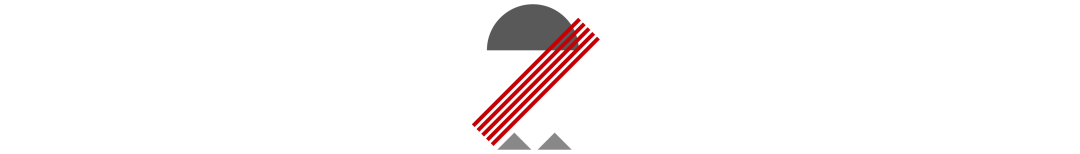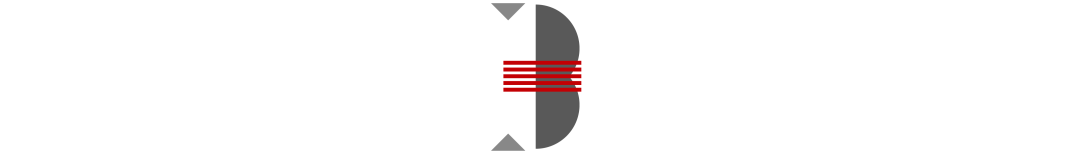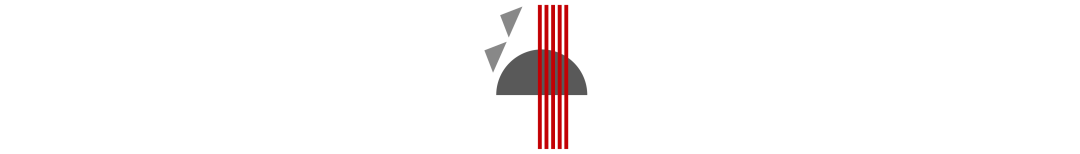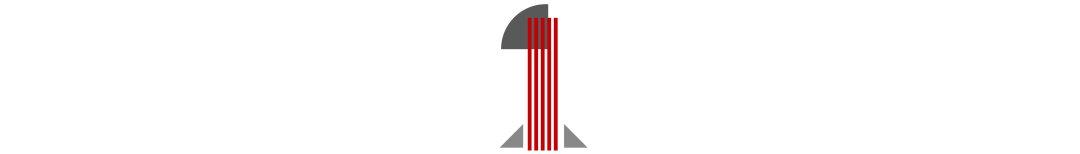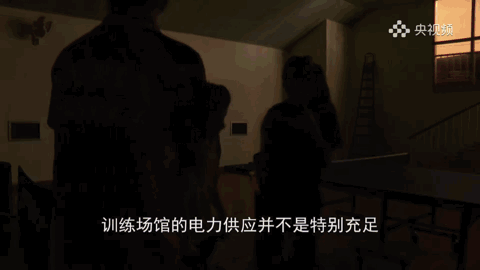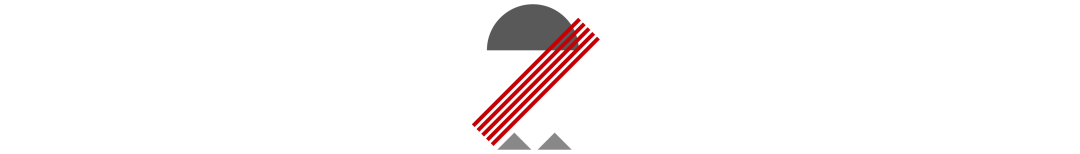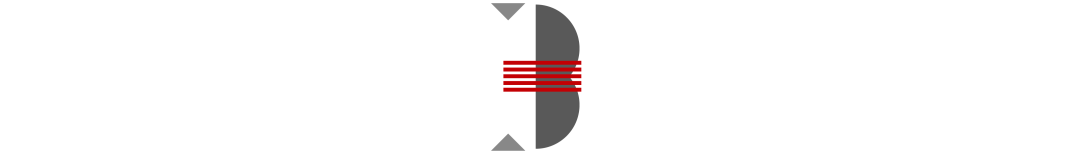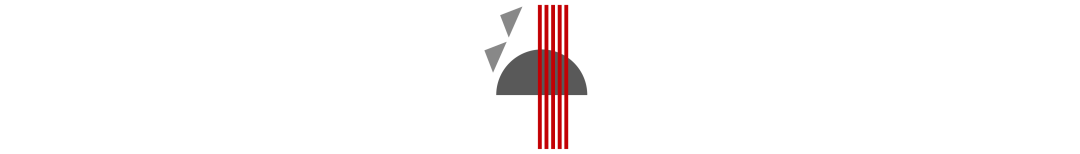比赛的双方,一个是39岁的奥地利老将,一个是年仅12岁的女孩。
这是她第一次站上奥运赛场,每个球都卯着全身力气去打。
可双方实力悬殊,仅24分钟,她就以0:4的结果输给了对手。
这也意味着,她的奥运之旅,才刚刚开始,就宣告结束。
600多万难民,陷在战争带来的贫困、恐惧、流离失所中。
我们总能在电影、纪录片里,看到中东小孩因习惯了暴力,拿着各种自制“武器”,玩着打打杀杀。
如果不是5岁那年接触到乒乓球,扎扎的童年,或许也会如此混乱。
艰难的岁月,打球,成了这个小小孩子心中唯一的精神支柱。
40度的高温,不通风的场地,空调是无法企及的奢望。
梦想有一天也能像丁宁一样,登上奥运赛场,成为世界冠军。
因为出色的成绩,她参加了国际乒联西亚地区奥运选拔赛,赢得冠军,成功拿到东京奥运的入场券。
在那200多个国家,1万多名运动员中,仅有6人的叙利亚代表团,显得尤为伶仃。
扎扎的比赛结束后,一位路透社记者,路过叙利亚大马士革青年乒乓球俱乐部。
破败的场馆外,几个稚嫩的孩子坐在树荫下,等待室内恢复供电,以继续训练。
原来,在那个国家10年的巨大创口中,一个登上奥运赛场的名字,就足以燃起所有人的希望。
其实今年奥运,还有不少运动员,背后都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
7月31日,希腊举重运动员亚科维迪斯在赛后接受采访,突然泪崩。
可他的国家,因多年经济危机,难以维系对运动员的培养。
他没有收入,每月仅能从体育联合会领到200欧元(折合约1500元人民币)。
那个能举起几百斤的高大身躯,就这样无力地在全世界面前跪下。
2019年11月,为了参加原定于去年夏天召开的奥运会,南苏丹代表队,提前7个月就到了东京。
至今仍在燃烧的战火,让这个非洲小国成了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60%的南苏丹运动员其实连一双鞋都没有,每天只够吃一顿饭,但我们会在沙子跑道和崎岖的泥地里拼了命地训练。”
唯有南苏丹运动员,回不去战火连天的家乡,又困于弥漫的疫情。
还有东京奥运开幕式上,那紧接在意大利代表团300多人后,仅有4人的伊拉克代表团。
他们安安静静走过会场,在周围热闹的人群里,格格不入。
不禁想起,11年前的广州亚运会上,那个孤独的身影。
要说奥运会开幕式上,最心酸的一幕,莫过于那支29人组成的“难民代表团”。
即使在比赛中得了奖,身后升起的也是奥林匹克会旗,奏响的是奥林匹克会歌。
23岁的尤斯拉·马尔蒂尼,来自叙利亚,4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游泳。
她眼睁睁看着一枚炸弹掀开训练场的屋顶,两名游泳运动员当场殒命。
在逃往希腊的海上,只能载6人的小船,塞满了20个难民。
四下漆黑的夜里,马尔蒂尼和3个会游泳的同伴跳进海水。
奋力推了3个半小时的船,才终于抵达岸边,救了全船20条命。
逃出生天的她,在塞尔维亚、匈牙利的田野里睡觉,在柏林的难民营里过活。
26岁的贾马尔·默罕默德,是田径1500米运动员。
24岁的跆拳道运动员阿卜杜拉·赛迪奇,出生在塔利班占领时期的阿富汗。
战争让他的国家千疮百孔,为了练跆拳道,他不得不逃往欧洲。
就这样逃亡了4个月,他得以在比利时的难民营里落脚。
可当他终于踏进了梦想中的奥运赛场,新冠疫情,又带走了他的母亲。
那些难民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在危险中苦苦求生,拼了命换来今天参赛的机会。
就像那个难民代表团中的南苏丹运动员詹姆斯·尼昂·奇恩杰克。
在竞技体育场上,培养一个世界水平的运动员,需要的投入太大了。
看看奥运奖牌榜吧,排在前列的哪一个,不是现实中的大国、强国。
而那些排在末尾的国家,也在现实中,渺小得听不见声音。
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只有刘长春孤零零一人。
“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望君奋勇向前,让我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义勇军进行曲》无数次响彻奥林匹克赛场,没有人再质疑我们拿冠军的能力。
这一届难民代表团,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服装,是由恒源祥定制的。
外套的蔚蓝色,是为他们送去宁静的希望,不再漂泊他乡。
想起2019年的军运会上,一向“凶猛”的国乒队,在面对斯里兰卡运动员时,出人意料地温柔。
不断让球、收力,还在观众为对方喝倒彩的时候示意现场安静。
那个印度洋岛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更没有与国乒队同日而语的实力。
这注定是一场必赢的比赛,所以我们想给困难的对手,留一点体面。
自己的声音曾被忽略,所以无法装作听不见别人的呼喊。
我们也希望,那些地图上不起眼的国度,能有更多人的努力被看到。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翎南会):奥运最心酸一幕,12岁女孩撑起一个国家的希望:看了她,才读懂巩立姣的眼泪